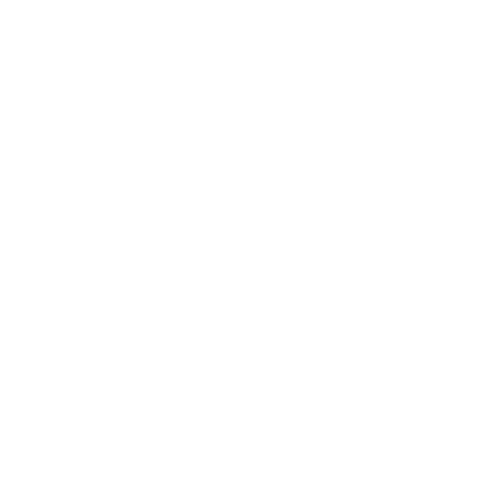撰文—林珈綺|圖片提供—香月、wendy
尊重與理解彼此的差異
是我們都能自由的原因
禁錮的時代遠去,基本人權不再受限,我們可以視自由為理所當然。然而,自由的邊界不因時代推進而自然開放。解放不自由之事,一直都是依靠人們意識到邊界、去理解問題,才能解放其中的不自由。德國的記者的卡羅琳.恩可在《差異自由消失的年代》一書中分析道:「精確使一切有所區別,讓你從一個人多樣、矛盾的個性與傾向,分辨他的人格本質。如果暫時削去輪廓,讓個人暫時無法分辨為個人,只留下一個模糊的集合體成為仇恨的接受者⋯⋯仇恨瞄準了仇恨的對象,它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仇恨來自模糊,故意不理解,甚至曲解真實,才能使仇恨如此「肯定」。很幸運我們可以生在自由的時代,然而正因習慣自由,更應小心保護它,並持續釐清那些不夠自由之事。
[TW] 刺青創作者 謝溫蒂 wendy
生於1995年。以刺青為主的創作者,雖然不是在臺南長大的臺南人,但小時候的確都吃牛肉湯當早餐!平常都在畫畫、聽音樂,是愛講話的E人。
Instagram:wendyisdead
[JP] 刺青創作者 香月
生於1994年。在「ONE MAN TATTOO」(現:臺中)開始刺青活動。目前不定期駐點在東京高圓寺的「TOKYO HARDCORE TATTOO」和臺北的「太陽龍宮」,活躍於國內外。 ©Yuki Aizawa
Instagram:lui.kazuki
來自臺灣的「wendyisdead」是wendy的Instagram ID,當年創帳號時處於emo狀態,取了聽起來很中二的名字,沿用至今。而出生日本的香月,名片上的4個角落分別寫著「長壽、感謝、繁榮、敬意」是對自己的期許,其中長壽指活到做完想做的事為止。他們目前都是刺青藝術工作室「太陽龍宮」的一員。
和大多數臺日小孩一樣從小看卡通動畫長大,wendy小時候有次去看迪士尼話劇,回家後照著記憶畫下來,媽媽驚嘆原來女兒會畫畫!從此確立了她的興趣;而香月則受到哥哥啟發,小時候模仿愛畫畫的哥哥所繪,加上經常看動畫,開始臨摹角色。
從畫畫到刺青,是偶然堆積的過程。香月先是被非繪畫的藝術形式影響,再意外接觸到刺青,一路上他看見了日本沒有的刺青文化,「我很喜歡音樂,喜歡的樂團都會刺青。另外,小時候在澳洲生活時認識的臺灣朋友Jason,離開澳洲後去美國從事刺青工作。大學畢業後,他剛好回臺灣,就邀我去臺北學刺青,讓我辭掉了原本已經獲得內定的工作(笑)。」沒想到wendy也有相似的脈絡,「小時候就聽龐克、重金屬樂,他們身上都有刺青。我覺得既然沒辦法玩音樂,只會畫畫,刺青可能是能最靠近這些文化的契機。從美國學插畫回來後,剛好有朋友在這個產業,也覺得把自己的圖刺在別人身上很帥,就開始刺青這條路。」
今年(2024年)3月香月接待wendy到東京展開刺青巡迴,也是她第一次去東京幫人刺青。一路上邊玩邊刺,最後,她在IG下了一段註解——”a dream tattooing in this cyber city”,在充滿奇幻異想的城市中,收穫了許多。旅程期間,抓住他們在出門前的早晨,一起描繪兩地的社會框架。社會氛圍漸漸開放的今日,從事以往被視為反叛的刺青工作,在現在是否依然會受到無形或有形的限制?
心碎的父母
「我從小就跟爸媽說長大後一定會去當刺青師,他們多少有一點心理準備,但真的去刺的時候,他們還是心碎了。」擔心客人背景複雜,父母一開始很緊張,wendy說當時只能用時間證明。雖然心碎,但還是有點好奇,最後媽媽讓她在自己的身上練習。
而香月家本來連染頭髮、穿耳洞都不允許,更遑論刺青,「我家就跟一般亞洲家庭一樣,他們說如果你敢刺青,就斷絕親子關係。」所以有段時間香月在家不穿短褲,回家都會注意刺青的地方有沒有好好蓋住。只是限制總是用來打破,「有次工作太累回家就在沙發上睡著了,隔天醒來爸媽就坐在旁邊,對到眼時想說完蛋了。」
wendy的刺青作品
香月的刺青作品
定型的印象
一開始,其實香月是害怕刺青的。
2014年至2015年日本有刺青師因替人刺青被起訴,原因是非醫師卻涉及醫療行為,而刺青是否為醫療業務成為爭議,直到2020年最高法院才裁決無罪。史書《日本書紀》也記載,日本在西元前就以刺青懲罰罪犯的歷史;到了19世紀,黑社會則開始將刺青作為加入幫派的入會形式之一。
因此刺青等於罪犯與黑道的印象,依舊深植日本大眾心中。即使到了現在,超商店員、餐廳員工,甚至一般上班族,仍難以看到他們刺青,生活上泡錢湯甚至租房子也可能受限。香月認為這樣的現象是有原因的,「無論哪個國家都會把一些東西非黑即白地斷定是好是壞,對日本來說刺青就是這樣,大家直覺地把刺青和非法行業牽扯在一起。」刺青在生活中不常見,大眾對刺青的不理解,逐漸織成恐懼的屏障。幸好,近年多虧社群平臺傳播,可以接觸到刺青的機會、年齡更廣,願意跨出刺青第一步的年輕人變多,大眾對刺青的印象有稍微鬆綁了。
wendy也覺得這次去日本是在最正確的時間,「原本聽說日本刺青圈很保守,加上師徒制嚴格,聽說國外刺青師要在日本刺青是很難的。但疫情後,許多刺青師開始報復性旅遊工作,硬生地打開日本的刺青市場。」於是現在有許多人和香月一樣,開始接待國外刺青師,讓日本顧客看見除了傳統風格外,更豐富多樣的刺青風格。也因爲東京是大都市,客群多元,這次旅程中wendy國內外客人各半,相比臺灣還是多為國內客,雖然風氣還是沒有臺灣興盛,但文化已長成多元豐富的樣貌。
時常往返臺日,香月也觀察到,「雖然沒有像臺灣一樣開放,甚至之前有看到在臺的日系企業員工可以刺青⋯⋯,但日本對於風格的敏感度還是比較高,接受多樣化的新設計與新趨勢的態度積極,刺青時有更多能凸顯個人品味的風格可以選擇。」
理解所以自由的時代
「以前覺得做想做的事就是自由,我最近有更深的體悟——尊重不同文化也是種自由。就像戰爭的發生,通常是因為無法接受對方文化。再把範圍縮小些,回到職場或朋友之間,如果沒辦法接受與自己不同的人、想要去否定對方的話,其實就犧牲了彼此某部分的自由。反之,懂得去接納不一樣的人,那彼此就能各自自由。」香月說完,wendy馬上大喊:「就是《進擊的巨人》啊!你們這些瑪雷人怎麼會懂帕拉迪島人的心情。就像中國和臺灣的關係。」可惜香月還沒看這部(笑)。
wendy倒覺得臺灣現在滿自由的,想穿什麼、刺什麼,已經不太會被人說話,議題也能夠好好發聲,或許是因為文化生態從大眾走到分眾,每種文化有了各自的擁護者,「現在好像沒有說哪一種風格最流行,已經不是單一審美,即使女生穿得很龐克、肉肉的,在今天都是可以被欣賞的,只是可能不是氣質型的(笑)。」待過美國,她覺得雖以外表打扮來說,美國確實更自由,但同時也非常追求政治正確,說話會怕冒犯到人。而臺灣當然存在許多負面的輿論,然多不是源自仇恨,反而也是因為不認識、不理解,心情上都還是善良的。
看待刺青的態度,wendy覺得可以更放鬆,「除了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刺青也能是放在身上的飾品,如一條蛇跟著肌肉線條去裝飾。最重要的是刺完後,這個刺青讓你變得不一樣了,你會越來越喜歡自己的身體。」香月也覺得刺青的心情很純粹,其實就是讓自己開心,更是一種自我滿足。比起擔心刺青一去不復返,他們看待身體就像畫布,只是每一張都獨一無二,「隨著每個人皮膚狀況不同,同一個圖呈現的成果也會不同。而從刺下去的瞬間起,圖就一直在改變,過個幾年再看又會變成完全不同的樣貌。」香月認為刺青的特殊在於不停地轉變,是這個媒材有趣的地方,也是與其他藝術形式最大的不同。
.
.
.
欲觀看完整內容,請購買 第43期〈Taiwan ⟷ Japan 20代的我們〉(*ˇω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