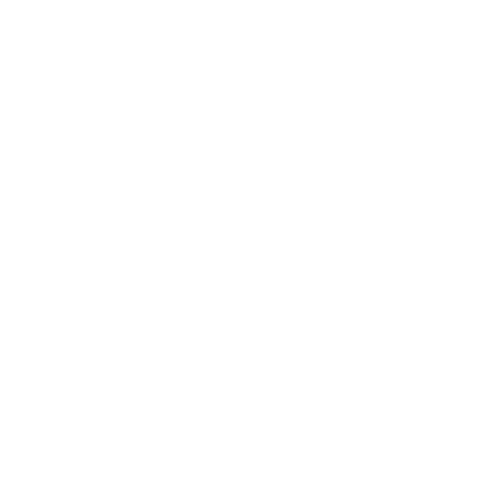撰文-蔡綉敏
「她」們幻變著目光躍動於銀幕之上,各色身姿陪伴我們共度陰雨白晝與黑夜星辰。當女子們的生命經歷悄然播映,我們入座,拓展日本電影中的女性面貌,也從中細探自己的性別倒影。
1960s,女人有了面具
《薔薇的葬禮》( 薔薇の葬列) | 1969 |松本俊夫
——「她生前最愛薔薇了,而且是假花。」
1960年代的東京,「Gay Boy」Eddie戴上假髮、假睫毛,舞動、穿梭於變裝酒吧與左派青年集會,踩上城市的街道,高跟鞋喀喀作響,彷若伊底帕斯王的弒母往事圍繞,凝縮時代壓抑卻又暗滔洶湧的焦慮與慾望。
日本第一部以地下男同性戀文化為題材的電影,由一群男人打造女人的面具與軀殼,革命的新浪潮,學運跟妓院離得近,他們討論青春與愛情的保鮮期、人的假面、抗爭與生活。作為「假女人」而存在,比女人(真花)更永駐,以唯美的死亡走向自我消亡。
*延伸選片*
增村保造《卍》同有性別辯證,女同性愛的迷宮,其塑造的時髦自我的女人與本片的「假女人」一般,成為戰後日本電影裡最具現代意識的女性形象。
愛自己,也是一部愛情故事
《轉校生》( 転校生) | 1982 |大林宣彥
——「我是妳,你是我。」
青春期少男少女交換靈魂後的「性轉」設定開啟,是青春開始轉變的契機。主角一美與一夫在對置的身體中,被迫演出另外一個性別/性徵的自己,這段似夢的成長經歷透過反覆操演,更理解彼此真實的性別處境。
若性別教育是將身體視為一座學校,主角的「轉校」,互相變身,到最後兩人已經分不清男女你我,少女成為男人婆,化為反擊社會框架的性別武裝。正如我們總在不斷改變的身體/身分中調整自我,在安身之後,得以告別青澀,長大成人。
*延伸選片*
大林宣彥《鬼怪屋》除了二戰怨念,也充斥著滿滿美少女,污泥中的純情,將少女這具身體拍成一部難以定義的奇片。
誰管女生不女身
《新宿好T 們》(Shinjuku Boys) | 1995 | Kim Longinotto & Jano Williams
——「她們被女顧客視為理想男人。」
1995年的東京新宿,絢光流溢,3位在瑪莉蓮酒店擔任公關的おなべ(ONNABE,指具有男性認同、裝扮成男人的生理女性),她們在家庭與職場中的樣貌,以及對女性、性慾、變裝、女同志的看法各異,呈現出日本女性的多元情慾,陽剛與陰柔氣質間的複雜光譜,展示90年代的同女之身。
許多日本異性戀女性來到瑪莉蓮酒店尋找另一種溫柔。他們作為「我」不陽剛,亦不陰柔,拍著粉,裹著「神仙束胸」當個中性人。自此「跨」出性別二界,當上「別人」。
*延伸選片*
同雙導演作品《夢幻女孩》。取材自寶塚歌舞劇團,講述當年紅極一時的生角森家秋、安壽美羅和真矢美紀,做為舞臺上的生角與舞臺下日本大男人主義劇場下永遠的旦角。
她們有自己的房間,還有家
《東京小屋的回憶》( 小さいおうち ) | 2014 |山田洋次
——「我的秘密,關在那個東京小屋的回憶裡。」
在一段跨越昭和、平成兩個時代的家庭故事裡,女傭人多紀於戰火煙硝中觀察女主人的日常生活及戀愛,那些被所謂國族歷史的「正史」所吞滅的一個日本女人的二戰回憶錄,同是時代下的女性私密史。
女性的身體總是與屋子/家庭綁在一起。位在東京山坡上有著美麗紅色屋頂的小屋,她喜歡喝紅茶,閱讀《亂世佳人》,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女性情慾終於釋放,無分女主人抑或女傭,這段鎖在心房的秘戀羅曼史,終歸令她們於亂火之中保存了「自己」。
*延伸選片*
小津安二郎電影《晚春》、《彼岸花》、《秋刀魚之味》皆同此片反映出戰前/戰後生活中女性於家庭的日常生活與困境。
成為母親,MOTHER不是MURDER
《午夜天鵝》( ミッドナイトスワン) | 2020 |内田英治
——「我現在是女人了,可以當你的母親了。」
在新宿的人妖秀舞廳,一邊賣笑、一邊跳著蹩腳的天鵝湖的「她」,遇見了愛芭蕾的寂寞少女。一個是午夜醜小鴨,一個是新宿烏鴉,她們成為彼此的家人,在「不對的齒輪」、「不對的身體」裡成長,奮力飛翔。
少女抱著漫畫《亂馬二分之一》,做浮在海面上天鵝的夢,曼妙舞姿繼承著她的想望。男兒肉體的「跨性別者」成為母親,養育著少女的「芭蕾天鵝湖」。無論是白日或是黑夜,在這個世界,跨性別者長著一對翅膀,轉瞬即刻,都是美麗。
*延伸選片*
由荻上直子執導的《當他們認真編織時》,片中亦道出許多日本社會對於跨性別者、LGBTQ社群的歧視問題。作為日本電影的性別教育嘗試,也為愛與家庭定義不同的面目。
蔡綉敏
1995 年生,長年影癡與老派文青,出沒於各式影展,文章散見於《幼獅文藝》、《紙飛機生活誌》等刊物,合著有《遇見文學美麗島》、《尋蹤:走讀彰化文學故事》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