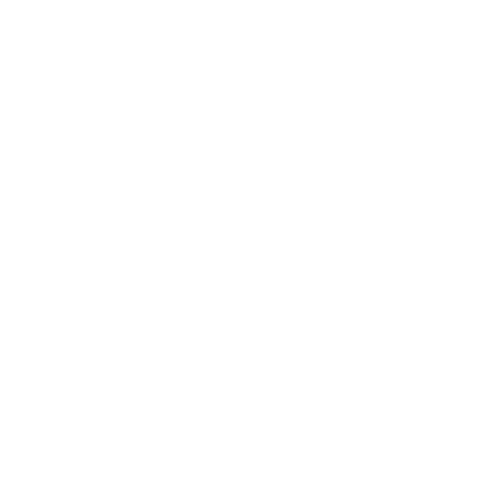撰文—陳瀅羽、攝影—蔡耀徵、圖片來源—Studio Ghibli、場地協力—薄霧書店
阮光民第一次接觸的吉卜力是錄影帶版的《天空之城》,片尾曲「伴隨著你」(君をのせて)響起,天空之城的大樹保護著飛行石往更高的空中遠行那幕,至今都令他相當觸動。
吉卜力的神奇毛毯
從「世界名作劇場」開始編織
早期宮崎駿和高畑勳在富士電視臺上繪製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而這個時期的作品,奠定了吉卜力美感的基礎與說故事的手法。像《天空之城》中,在隧道工作的男主角巴魯嚮往著天空之城;而女主角希達佩戴的飛行石,卻和地底礦石相互呼應,「這巧妙的設計,就是『表現』故事的功力。」阮光民以漫畫家視角,解構吉卜力值得反覆回放的理由。
雲林出生的阮光民在看宮崎駿作品時,總會注意到其中隱含的大自然元素,「土地的形象就如同《天空之城》中的大樹,代表永恆的包容與存在,不論是象徵科技的巨神兵,還是眾人搶奪的飛行石,無一不被『大樹』擁抱著。」阮光民透露如孩子般的純真說,「宮崎駿的敘事手法讓觀者像是躺在剛曬好的棉被上,暖暖的,引起我們對故事的共感。」
像日本動畫導演新海誠雖然構圖美豔,卻難掩科技的銳利感,「但吉卜力則是一張波斯地毯,除了帶有異國色彩之外,未收斂的毛邊也是作品迷人之處。」阮光明形容,吉卜力的樹即便不完全寫實,卻充滿生命力,這種溫度難以用科技繪製取代。
截然不同的作業宇宙觀
一人獨立工廠vs大型手工業
同樣是畫作,對「個人作業」的漫畫家來說,從故事發想、分鏡、繪製得一手包辦,而「大型工業」的動畫電影則是依賴細緻的分工,導演結合繪圖師、著色師、動畫設計、音效、音樂等,完成精密的鋪陳。阮光明進一步分析,以「喝水的動作」為例,漫畫家會處理成「一個杯子」、「手拿杯子」、「杯緣靠近嘴巴」,三個場景;而動畫則要思考杯中的水紋晃動,喝水的音效,顏色的明暗表現水位變化等等。創作的出發點不同,其手法也隨之改變。
在人物建構上,漫畫的人物外型是存檔在作者腦中,但動畫必須先繪製角色的多面圖,讓團隊清楚掌握形象。阮光民笑說,細看吉卜力的人物造型上都比較簡單,「如果每一個都要像井上雄彥《灌籃高手》中的樣貌,那可能就要悲劇了,因為只要一個神韻不對,很容易被觀眾察覺。」
吉卜力製造
想像力的品質保證
「任何幻想的事物其實是建立在實體的變形,或許在未來都會被建造出來。」阮光民觀察,宮崎駿故事中的飛行器,巧妙結合生物形態,配合支節傾斜與昆蟲擺動翅膀的飛行方式,創造看似熟悉的新奇感;或細看霍爾的「移動城堡」,會發現建築元素皆來自日常的房屋、大砲,「但宮崎駿厲害之處在於重新拼湊後,成為和諧又可愛的新東西。」這不只讓每部作品的世界觀,成功烙印在觀眾的心中,更創造無數個吉卜力代表性的符號。
「即便吉卜力動畫作品極為豐富,依舊預留給觀者高度的想像力。」雖然漫畫與動畫的創作歷程截然不同,但對於吉卜力挑戰最新的3DCG技術,阮光民卻舉雙手贊同。在面對充滿挑戰的未來時,漫畫與動畫仍舊走上了交界,就像線條世界裡充滿幻想的無限可能,無論是將漫畫真人化,或動畫3D化,創作者們永遠是愛做夢的主角,持續用畫筆與色塊實現腦中異想藍圖。
阮光民
1973年出生於雲林斗六,其作品大多描繪臺灣社會的獨特溫馨故事,尤其擅長刻劃人情義理、捕捉家族、親子、人性糾葛等微妙情愫,以幽默溫暖的方式呈現濃厚的人文關懷。
歷年來多次榮獲大獎肯定,而作品《東華春理髮廳》與《用九柑仔店》亦改編成偶像劇。並跨界合作舞台劇《人間條件》漫畫版及《天橋上的魔術師》圖像版,今年《用九柑仔店》也即將以舞台劇的方式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