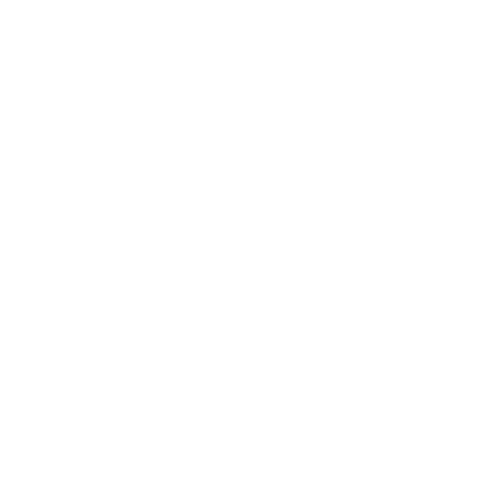撰文-麥恩、拍攝-張天駿
8月的第一週,有三組日本創作者不約而同,久違地,來到台北。
作家伊坂幸太郎,出道第25週年,睽違13年再度訪台,帶著他的新作《樂園的樂園》,以西遊記為引描繪AI末日後的世界;歌手齊藤和義,首次海外演出就獻給台灣,和伊坂幸太郎像是創作上的靈魂伴侶,一曲〈幸福的早餐無聊的晚餐〉甚至讓他下定決心辭職,成為全職作家;最後,是日本歌姬濱崎步,等了17年,再度登上台北小巨蛋,「那我應該要和濱崎步當朋友呢!」伊坂幸太郎開玩笑地說,這樣下次可以早點一起再次訪台。
一點點就好的幽默
即使筆下有入選「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的《重力小丑》、受多次改編的《死神的精確度》、翻拍成好萊塢電影《子彈列車》的《瓢蟲》等經典作品,伊坂幸太郎參與過的公開活動卻不多,在日本更是屈指可數。
伊坂幸太郎自認不擅長公開談話,卻總悉心準備,訪台前還和AI討論閒聊素材:「它說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都喜歡手機成癮的話題,只要說昨晚我邊做夢邊滑手機,大家一定會很感興趣的!」結果無論是在採訪或飯局提起,都沒有人起反應,冷場反倒成了另一種笑點。
「我覺得讓大家笑得出來,是溝通方式中最好的一種。」無論話語或書寫,伊坂幸太郎都保持如此作風,就連筆下的殘酷殺手、冷血死神都因不諳世俗而沾染了點幽默色彩。他說自己沒有特別的創作技巧或公式,娛樂性難去強求,但笑料取自生活,小小的便足夠,「不管是自己的創作,或是我喜歡的作品,如果沒有那一點點的趣味在裡面,就會感覺少了點什麼呢。」
來自創作的創作
伊坂幸太郎喜歡音樂,總為自己的小說配上幾曲,《再見,黑鳥》書名取自名曲〈Bye Bye, Blackbird〉、《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的主角把「衰」歸咎於巴布狄倫的歌,《Golden Slumbers:宅配男與披頭四搖籃曲》更直接以他最愛的樂團披頭四的同名歌曲為靈感創作,甚至採訪這天,就穿著印有該專輯《HELP》封面圖樣的T恤。(而他最喜歡的歌是〈No Reply〉,但也擔心自己沒說好,被別人誤會成是他不想回應。)
他的小說裡也能看到其他作品的身影:《白兔》帶著《悲慘世界》作者會突然冒出來的筆法、出道作《奧杜邦的祈禱》裡的旅鴿則是來自漫畫《哆啦A夢》——伊坂幸太郎甚至記得是第17集的〈大鴕鳥多多鳥再見〉。而他筆下最著名的小偷(或偵探)黑澤,則是和導演黑澤清的小小致敬。
「故事寫久了,名字會開始不夠用,所以就找喜歡的導演,借用他們的名字,換一下拼法,當作故事裡的主角。」伊坂幸太郎說,第一次看到黑澤清,是1999年電影《神木》上映,導演來到仙台辦講座時。他談吐沉穩,謙虛和善,電影更是精彩,「他非常了解藝術和電影的本質,無論動作、恐怖或各種風格,都能掌握得住電影的美學,兼具娛樂性與藝術性,那對於創作者來說是非常理想的狀態。就算題材非常嚴肅,黑澤清依舊能在裡頭帶入些趣味性,這樣的作風讓我很有共鳴,也是我想朝的方向。」或許正因如此,伊坂幸太郎的筆調總是輕快地佈局、以日常書寫奇幻,偶時哲理,偶時又冷不防地來了一發冷笑話,讓讀者看得津津樂道,把他獨有的風格喚作「伊坂流」。
你所期待的伊坂流⋯⋯?
「其實我沒有特別意識到自己的風格,但我覺得有作家風格是件好事,不管電影或小說,都會有作者的某種風格在裡頭。我知道有些讀者來說風格不重要,只想看到好看的故事,不過對我而言是件蠻重要的事。」伊坂幸太郎說,作品能在讀者的解讀中推敲出脈絡,是件很榮幸的事。
最一開始,伊坂幸太郎以「推理小說家」被多數的讀者認識,但他的創作從不止於推理,甚至每一本風格、類型、題材都不盡相同,驚喜許多,不過也有熱衷於推理的讀者感到水土不服。近五年,他漸漸發覺自己的小說已經培養出一票讀者,同時也萌生一個疑問:「如果大家花錢買我的創作,看到的卻不是他們期待的該怎麼辦?」不想重複自己,也不想背叛讀者的期待,書寫必須在自己的風格與想寫的方向間取得平衡。那,伊坂幸太郎覺得他的風格是什麼呢?
「啊,好難的問題。」他皺著點眉吐槽道,「我也是看讀者的回饋才知道,蠻多人喜歡我作品中一些特別的角色、脫離現實的設定、一個一個被收回的伏筆,才發現『原來這些是我故事裡的特色!』而在創作時,我總在想,要怎麼帶給讀者驚喜,所以就結果而言,算是我的喜好變成了風格呢。」
變成老爺爺也要繼續寫下去
不過低潮依舊有,特別是近年更在乎讀者的感受後,每當遇到其他創作者提及欣賞的、導演想翻拍的多是早期的作品時,伊坂幸太郎總會想:「其實我現在寫的作品也很好呀,為什麼大家都提到早期的作品?會不會是我一直都沒有突破呢?」
不過伊坂幸太郎低潮,被老婆的一句「你在50歲的期間有個50歲的代表作就好啦。」點醒,讓他意識到無需急著證明自己。老婆就像他的人生導師,總在最困窘的時候一語道破些什麼,當年糾結若為專心撰寫《重力小丑》而離職,會不會帶給家庭過多負擔時,也是她一句「很好啊!」才讓他放下心中的大石,成為如今的伊坂幸太郎。甚至揣想,當年若《奧杜邦的祈禱》沒有得獎,從未正式出道,也依舊會走在寫作這條路上,「前陣子就被她說反正變成老爺爺還是會繼續寫,真不知道是在鼓勵我還是抱怨我呢。」他打趣地說,「寫作真的是我唯一的興趣。」
瓶頸沒辦法說突破就突破,終究得等靈光自己從生活中找上門,《樂園的樂園》裡與AI相對的NI(Natural Intelligence)就是伊坂幸太郎和作家凪良汐聊天時誕生。她隨口問了句「你要寫的AI是電腦的AI嗎?」讓他驚覺,為何不曾想過有其他的「智慧」呢?而開展對於自然智慧的想像及書寫。他開玩笑地說,有時太幸運,一連迸發好幾個靈感,也會佩服自己:「哇!我是天才嗎?」
眺向遠一點的地方
言談間帶著笑料、小說不時向哲理專研,但伊坂幸太郎仍舊認為自己的視野是狹隘的,而總試圖將故事帶往更宏觀的方向,「我不認為自己看到的都是對的,很多東西是一體兩面,得從不同角度來看,像人類社會也是同樣的道理,當終點來臨,那是件壞事嗎?我想藉由《樂園的樂園》這故事來探討這個問題,若從另一個角度想,這或許是種重生。」
《樂園的樂園》的最後,伊坂幸太郎引了井伏鱒二的短篇小說〈山椒魚〉,三位主角坦然地接受「末日」。不過,他自己倒是挺擔憂的,「我滿害怕末日到來,但現在的世界氛圍下,我好像也不能做什麼,只能被動地接受,祈禱明天太陽還會升起,也告訴自己不用想太多,過好眼前的生活就好。」他說,故事裡的樂天是對自己的期許,那就像是拼圖與天氣,當你認真投入前者終究有辦法完成,後者則無論多努力終究無法控制——末日或許終將到來,但仍舊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
寫故事的伊坂幸太郎總保持3度的仰角,把憂慮留在思索中咀嚼,讓娛樂與對未來的想像展露於字裡行間。他相信,一點一點地累積眺望,一定會越看越高,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