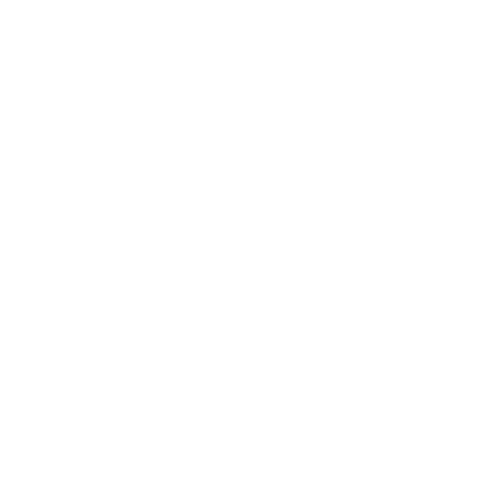撰文-林珈綺、攝影-鄭弘敬
中午時間,鑽進武昌街城隍廟旁的巷子,與洪愛珠和毛奇相約「添財日本料理店」。在外排隊有數人,年歲皆過半百,店裡更是熱烘烘,人客忙著吃飯講話,服務大哥、大姐像穿溜冰鞋,絲滑地溜來走去,不能擋著他們的路。為了拍到好看的畫面,攝影師在夾縫中求生存,向來去的客人、送菜的大姐頻頻道歉,食物面前,必須嚴肅。
今日的兩位食客,不只愛吃、會煮、還寫下來,對飲食各有自己一套。從她們的筆墨間,可以走入一座市場、蒞臨一間餐館、品味一道菜,這回藉著她們吃飯的技藝領路,走入她們與「臺式日本料理店」的回憶與日常,來回間,把定義疏通、情感歸位。究竟這個同時點得到炒水蓮與生魚片的地方,有哪些特異之處?
添財日本料理武昌店
創立於1957年,從小攤車開始,至今已在臺北車站附近坐擁兩個店面。訪談中洪愛珠提到:「添財一個品項基本上是別人可以開一家店的東西。」在這裡,你可以點到日本料理店基本的定食套餐、鰻魚飯、烏龍麵、握壽司、刺身,小菜如炸物、手捲、燒烤,當然還有招牌——關東煮,品項之多無法一一列舉,挑喜歡吃的便是。而吃飯時間客人總是絡繹不絕,大多還不是慕名而來,而是吃了幾十載,就這麼一直吃下去的客人。
臺灣人類學訓練,義大利慢食大學食物文化行銷與溝通碩士。食物研究者,住在臺北淺山;從事專欄與報導寫作,料理設計,著有《深夜女子的公寓料理》、《足夠好的日常》。 經營「深夜女子公寓的料理習作」社群。
臺北城郊養成、倫敦求學。資深平面設計工餘從事寫作,文章多及家庭餐桌、庶民吃食與人景。著有散文集《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一種都會風格
秋:最早接觸臺式日本料理店的記憶是什麼?
毛:我雖然在彰化出生,但自從上幼稚園後就一直住在臺中。幼稚園所在的中華路以前相當熱鬧,其中有一家叫做「和壽司」的臺式日本料理店,現在已結束營業。小時候常常在那裡吃手捲、茶碗蒸、土瓶蒸,那時覺得土瓶蒸是一道神奇的料理,湯倒出來料在裡面是怎麼一回事(笑)。另一間「水車日本料理」則是我認知到定食之精妙的啟蒙,雖然不是正統的日式餐廳,但裡面的炸豬排扁扁的,有點像排骨,是臺灣味。提到排骨,還有一家位於臺中市政府和議會附近的「後引日本料理」,雖然不是小時候去的店,更多的是議會的人談事情時用餐的地方。他們以滷排骨為招牌,雖然是比較體面的店,但味道一樣很臺。
愛:西門町美觀園的招牌菜色也是滷排骨。
毛:我覺得很有意思,後引比較接近我們今天吃的添財,水車就是介於和壽司和後引之間,比如我爸與叔叔兩家聚餐,就會在水車。
愛:我父系家族的長輩多是二戰前出生,青年階段以前,受的是日本教育,習慣以日文通信,訂閱日文雜誌,解嚴後頻繁到日本各地旅行。因對日本料理情有獨鍾,所以家族聚會常選日本料理店。在我們剛剛吃的添財的同一條巷子裡,以前還有一家「梅村」,當時就像小津安二郎的場景一樣,一個極窄的巷子,兩家很熱鬧的日本料理店,永遠都是滿的,開了快70年,幫長輩慶生,很喜歡來。記得我父親的60大壽就辦在已搬到衡陽路的梅村,傳統上幫長輩做壽會在中式餐館,不過考慮父系家族的偏好,改選這種比較鬆放不拘的形式。宴席開場就是一個軍艦型的巨大容器,盛滿切成極厚的生魚片,並以乾冰製造煙霧效果。這種呈現方式,毫不日本,但有經典臺式日本料理店的歡樂氣氛,是吃一份派頭。
毛:以前還有一間店很有名。我母親是在員林出生的,員林是一個中部比較富裕的小鎮。(愛:是全臺最)戰後外公、外婆經營著一間像迪化街南北貨的店,由於當時中部沒有像臺北有這麼多大餐廳,為了要賣貨,就需掌握當地總舖師的名單,她們也因此培養出好的味覺。儘管如此,她們仍然對於日本料理抱持著某種想像,姐妹聊天聚會都約在臺中的「養老乃瀧」,是當時很有名的連鎖臺式日本料理店。
愛:如果要請家裡長輩吃飯,萬無一失的選擇就是日本料理店和鰻魚飯店。請他們去吃西式絕對被打槍,中式他們也挑剔,可是日本料理他們是永遠開心。
秋:這種臺式日本料理店是否代表著比較有消費能力的階級去吃的餐廳呢?
愛:我倒不會覺得是階級,它是一種都會風格,在城內比較精華的地段才會有的餐廳。過去臺灣人也不吃館子,往前推至7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人都在家吃飯,會上館子還是因為社交需求,所以我感覺它是種都會風格的產物,也滿時髦的。
秋:什麼時候會想吃這種臺式日本料理店?
愛:想要什麼都吃一點時,就會想起臺式日本料理店,比如添財,就是我們的家庭飯館,它一個單一品項,都能拿去開一家專門店,且因調味上較少辛辣或刺激的味道,孩子可以吃的東西也相對多,像是烤魚、茶碗蒸。來這裡也有點小犒賞的意味,不需正襟危坐,但想吃些好吃的就會想來這種,能夠同時點得到炒水蓮和生魚片的地方。
毛:臺式日式料理也是我家的甜蜜點,爸媽雖然分別來自彰化的員林和社頭,可說是臺到不行,但他們最大的交集還是在日本料理。比如說今天不想要煮飯的時候可以去外帶握壽司回家吃。
秋:你們會用哪一道菜去評斷一家臺式日本料理店?
愛:我一定會點高麗菜捲。因為奶奶受日本教育,每年過年前都會做上百捲高麗菜捲,是我們家的年菜。如果要在外頭吃的話,添財和華西街夜市的「壽司王」是不錯的選擇。有些店的菜捲是批來的,但他們是自己做,比較用心的店都自己做,因為做菜捲其實很費工,需先提著葉子一片一片燙,以防裂葉,燙完後包餡,那個是花時間的,所以菜捲還是一個關鍵。添財的高麗菜捲很特別,在家裡做,為了讓餡料豐實,裡頭魚漿與絞肉會包很多,可添財完全反其道而行,菜捲超厚,好像一個很瘦的人穿很大的羽絨衣,中間只塞一點點魚漿,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們解釋道因為高麗菜甜!吃高麗菜捲是為了吃高麗菜,不是吃餡子。我後來覺得這是另一種美學,雖然自己在家裡做還是會加很多餡料,魚漿甚至加入干貝,但是添財的菜捲吸飽湯汁,冬天吃尤其合適。
毛:我也認為是菜捲,還有甜不辣,可是我必須說,小時候我是不懂它好吃在哪裡(笑),因為它的口感不明確,有點Q又不Q,好吃不好吃也差滿多的,可是長大就好了。其實我們在講的甜不辣在日本是另外一種食物,是炸的,經過了在地的轉換,變成一樣滿具代表性的臺味日食!
愛:我認為還有手捲。日本的手捲通常包捲米飯,臺式則一律包生菜絲,十分爽脆,而我竟更偏愛這種本土手捲。再加上臺式不帶酸、純甜的美乃滋,我剛剛還特別確認不是日本的KEWPIE美乃滋,有些還會加柴魚片。口味通常有單獨蘆筍、單獨蝦、蘆筍蝦,是我小時候覺得日本料理店中最好吃的東西,後來才發現它完全是土生土長的產物。我前一陣子在一家鰻魚飯店,吃到更奇妙版本的手捲。乍看店面裝修,本來無法判斷是日本還是本土品牌,然而一吃手捲,除了生菜絲,竟然包了壓碎的老油條,我是很震驚的。但屏除成見,味覺上竟不違和。海苔、生菜、老油條都是香脆材料,特別討喜。這完全反應了臺灣式的不拘一格(同時也是不求甚解)。
.
.
.
中略
.
.
.
臺式日本料理店的場景與未來
秋:回到臺式日本料理店,你們會覺得它在臺灣的各式餐廳中,扮演這什麼角色?
愛:我想到臺式日本料理店就是聚會,板前通常是1至2個人,基本上是不談話、很屏氣凝神的一件事,主廚上菜你就要趕快吃,有時連拍照都是冒犯。相反地,你可以把臺式日本料理當合菜,臺灣人很厲害的地方是,我們會把所有的菜系都吃成合菜,每個人都點一套定食,可是你永遠都可以偷夾對方的蝦或其他東西,是各自吃,可是又是一起吃。這種飲食方式是臺灣人的魂靈,基本上完全脫離日本而存在的,只是附著在日式餐館的形式裡頭。所以觀察添財裡面,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那一桌又一桌的三代同堂,臺式日本料理店裡三代同堂的氣息太強烈了!所以我覺得它會淵遠流長,因為它其實非常切合臺灣人某種聚餐的脾胃。
毛:臺式日本料理店是包容時間差的,很多餐廳就是要人到齊你才可以開始吃,可是臺式日本料理店你吃一吃再叫人來,都是可以的,因為有時候談事情就是這樣,先到的人先吃,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這種包容的彈性,真的是一種非常臺灣的用餐場景。
秋:當長輩們陸續離開我們,臺式日本料理店將會是一個舊時代的象徵,還是能一直存在下去的店?
毛:我想要稍微離題,成為臺北人後,我鄰居是剛好大學的老師,剛搬進去時,他送我一條「加納魚」,其實就是日本的真鯛,他說這個加納魚臺語念起來是「加蚋仔」(Ka-la̍h-á),因為以前臺北叫做凱達格蘭盆地,中年男人的浪漫就是會說嘴(笑)。這引發我的思考,到了我們這一代,對於臺灣的認同或歷史,其實已經擴充了更多理解,從日本時期到現在,當我們進到臺式日本料理店中,必定會召喚一些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情感,並且是其他類型餐廳沒有的。從商業操作或是觀光的角度來說,當外國朋友來,我還是會想帶他們來這種餐廳吃飯,並跟他說這個是我們會來吃飯的地方,因為它有一種很明確的風格、氣氛,那個氛圍是感人的!
愛:我覺得以這種店型旺盛、興旺的程度,其實看不到它有衰落的傾向。一個人就點蛋包飯、比較薄的豬排飯、厚的生魚片,年輕人有自己與它相處的方式,我想他們還是會很喜歡它的,只要臺式日本料理店一直是這種家庭餐廳的形式。我想也許菜單會有變化、遞嬗,與日本的日本料理逐漸脫鉤,發展出獨立的菜色,但不會式微,因為它已經改裝完畢,變成一種相當成熟的菜系。這種全民愛戴的程度有點像臺灣的泰國菜,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只有在臺灣能夠吃到的一個料理分支,且因改朝換代,永遠留在了這裡。這裡頭當然有殖民遺緒,是特定時空的物質證據,然而又切切實實地陪伴過臺灣好幾代人,早已成為了我們飲食生活的一部分。
欲觀看完整內容,請購買 第42期〈現在就想吃的 臺味日食〉٩(●ᴗ●)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