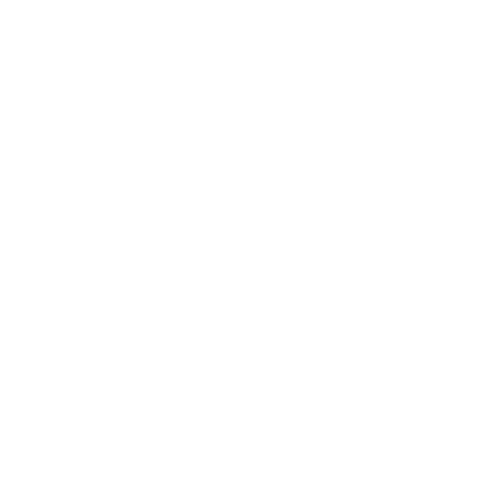文 / 新經典文化、圖 / Studio Ghibli
在吉卜力所勾勒出的動畫世界裡,究竟所謂的「天才」是什麼模樣?是導演的天馬行空,還是製片的慧眼識英雄?在第31期《秋刀魚》的〈吉卜力的世界,世界的吉卜力〉特輯推出後,再次與《釀電影》相會,在新經典文化最新出版的《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新書對談中,一同暢聊關於吉卜力三巨頭的各種秘辛。(本文出自 8 月 1 日新經典文化主辦之「從《風之谷》到《輝耀姬物語》-關於吉卜力,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厲害的事」線上講座)
什麼是「#宮崎動畫」?
(陳柏昌:主持人,新經典文化版權編輯,以下簡稱陳;張硯拓:《釀電影》主編,以下簡稱張;陳頤華:日本文化誌《秋刀魚》總編,以下簡稱Eva)
陳:這是鈴木敏夫先生口中泛指「宮崎駿導演的動畫」。吉卜力發展到後期,開始物色年輕的導演,有的可能是原作、原畫出身,如果要讓這些人進一步學習導演的事務,吉卜力的做法是:由製片方提供原創素材、分鏡圖等,再讓他們去進行,執行吉卜力想要的畫面。鈴木先生就把這些導演的作品,稱為「宮崎動畫」,比如:近藤喜文執導的《心之谷》、宮崎吾朗執導的《來自紅花坂》。
張:我對「宮崎動畫」相對不熟,可能跟心態上有關。來聊一個秘辛,這次《釀電影》的專題,大家如果重頭翻到尾,就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張宮崎駿的劇照,當然不是我們不想放,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斑斑血淚,跟吉卜力工作室溝通,但溝通的過程中發現了從來不知道的事情──我說我們要做宮崎駿專題,對方說:「請你們要做就做『吉卜力專題』,我們會很願意提供素材;如果只有宮崎駿本人專題,請不要這麼做。」但我們文章邀稿都寫好了。
交涉過程中其實很不理解為什麼,但讀了《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吉卜力勢必會有誰來接班的焦慮,在高畑勳與宮崎駿兩位大師之後,做為觀眾也可以想像這樣的焦慮,因為沒有人可以比他們兩個做得好,或是說:沒有人可以跳脫他們倆的風格。尤其讀到後半本,當鈴木敏夫開始一個個帶出新的導演,如近藤喜文、吾朗、米林……(陳:米林宏昌)你看我連名字都記不熟,難怪人家不給劇照。(笑)
好幾位都是從《風之谷》就共事了二十幾年,才被拔擢上來當導演的年輕人,你會發現鈴木敏夫在寫他們的時候都是百般呵護,非常想要為他們撐腰,相對來講提到兩位老人都是吐槽,真的是兄弟之間的描述方式。
這幾位年輕人是如何在兩位大師底下工作,漸漸爬上來,能夠活下來的人要嘛是對宮崎駿的要求言聽計從,甚至加倍回饋、沒有任何怨言,要嘛是很有想法、能夠跟大師抗衡,堅持自己的作法又能讓宮崎駿信服。很替這些晚輩感到險象環生。說是年輕人,老實講也都不年輕了。(笑)
鈴木敏夫很坦白地講,宮崎駿雖然常說:「我要給年輕人機會。我不要干涉他們。」但是忍不住還是東說一句、西說一句,動不動就要改。這就造成吉卜力後來作品,畫風、背景、人物動作,還是明顯跟我們熟悉的日本動畫是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屬於吉卜力的風格。用「宮崎動畫」來說這樣的東西,鈴木先生應該是憂喜參半的吧。只要上映,幾十億的票房都不是問題,可是它長得永遠就是「很宮崎駿」。
《輝耀姬物語》的製片人米林宏昌後來離開吉卜力,自己開了一間公司,做的《瑪麗與魔女之花》,它已經沒有吉卜力的logo,看完還是覺得那是一個宮崎駿打七折的作品。作為粉絲或是觀眾,完全可以感覺得到那個焦慮。不是焦慮這間工作室該怎麼存活,老實講,吉卜力只要賣龍貓的所有週邊玩具就是可以永續經營下去,但他們如果想要在藝術上有新的作品,要怎麼樣畫出來不像「宮崎動畫」,又有所謂「宮崎動畫」精神的東西呢?
讀到這些,我就好像比較可以理解他們堅持「要做就要做『吉卜力專題』。」不只是商業或名聲的考量。
陳:補充一下,米林宏昌第一次挑大樑時鈴木敏夫很擔心,請他畫分鏡圖,他畫得非常細,但如果真的照著導,會變成三四小時的電影。鈴木先生提醒他可以怎麼改,結果第二次改得非常好,如此來回幾次,終於有一天鈴木先生受不了問他:「到底為什麼要畫這麼細的分鏡圖?」他才說習慣了宮崎駿每次都修修改改、狂打槍,所以會一開始什麼都準備好。他們已經適應「宮崎駿模式」,還是會有顧慮,如何往下找適合的接班人。
宮崎駿與他兒子的「#父子情結」
陳:宮崎駿的兒子吾朗執導的《地海戰記》,一開始就是伊底帕斯情節。鈴木敏夫說道,最開始不確定吾朗能不能當導演,但宮崎駿答應了——如果吾朗願意,就讓他導。吾朗到底「能不能畫」?考驗的第一關,鈴木請他先畫一幕《地海》場景,馬上通過,據說讓所有相關工作人員都相當讚賞──大家都沒想過原來「少爺」這麼會畫圖。畢竟從小就看遍父親的作品,也會去深入研究。
Eva:我想先提一個跟吾朗本人沒直接的關係。(笑)
從影迷們的回饋來看,我們這次提問很多台灣讀者、甚至採訪了兩位香港觀眾,他們都會提到小時候喜歡《風之谷》、《天空之城》,長大後卻會比較喜歡《兒時的點點滴滴》和《心之谷》,會因年紀漸長喜歡不同的吉卜力作品。但是提到《地海戰記》,大家的反應都只是:「嗯⋯⋯。」「是想要推他的兒子出來吧?」(笑)
大家都看得到吾朗的努力,可是也很清楚看他想挑戰某些地位,不是指他爸爸的地位,而是在作品裡太用力想去強調什麼來留在大家的心裡。這部片真的很容易被大家歸類在「我們先不要討論它。」
讀這本書的時候,覺得吉卜力要跳脫這兩個大導演高畑勳與宮崎駿真的很難。吉卜力也在挑戰新風格啊,比如那個3D?我每次都記不起來那部的名字⋯⋯
陳:《安雅與魔女》。(笑)
Eva:對。看得出吉卜力的企圖心啊。當然,因為眾所皆知的影史票房第一名被《鬼滅之刃》超越之後,大家真的要重新認識吉卜力。這本書的最後沒辦法寫到最即時的狀況,可是看得出來他們正在替下一個十年做預備了。所以我覺得《地海戰記》與其說是「父子情結」,不如說是很好的「觀眾分水嶺」。
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調查,現在的二十代觀影的比較喜好《來自紅花坂》和《心之谷》這樣比較青春的電影,鈴木敏夫跟吾朗也有做一系列討論:是「青春」、「熱血」的主題到了平成到令和之間,在動畫電影上變得更必要了嗎?我們還要用這個公式看動畫嗎?還是30-40代觀眾沒有放開對吉卜力充滿想像的那顆心嗎?(笑)
張:我們的確很難想像,不要說很難想像新一代的觀眾了,我們隔著一片海,對日本文化既是鄉愁、又是外來輸入文化,我們要把對吉卜力的情感延續到後來的新人身上?日本跟我們同樣三十代的人們對宮崎駿的情感又跟我們一樣嗎?
尤其吾朗又跟其他的新血不同。我們有作為宮崎駿粉絲的情結,但他才是全世界對宮崎駿有最複雜情結的人。(笑)
剛剛柏昌提到的那一段,就是他小時候爸爸都不在家,他只能反覆看爸爸的作品,看爸爸的原畫然後反覆去揣摩,讀起來超可憐的。
Eva:好想哭⋯⋯。
張:這是怎樣的父子關係?只能從爸爸的作品去感受到我跟爸爸更接近⋯⋯。
剛剛說到的NHK幫高畑勳拍的紀錄片,再往前幾年,也有一部《宮崎駿:十載同行》記錄2006到2016年,重疊了吾朗在拍《地海戰記》的時候。
當《地海戰記》第一次做封閉型的媒體試映時,宮崎駿第一次看他兒子的作品。鈴木敏夫在書裡寫到,宮崎駿看了一小時就走出去,所有人都緊張得要死。其實沒事啦,宮崎駿只是去上廁所。(笑)
但如果有看《十載同行》就知道才不是這樣,鈴木敏夫根本是在為這個心疼的晚輩粉飾太平。紀錄片裡宮崎駿就是臉色鐵青地走出去,在外面的沙發抽了一根菸,一句話都講不出來,最後默默地進去把它看完。看完後只說一句話:「我在看我自己的兒子,但是他還沒有長大。」
我們對《地海戰記》的感受是什麼?我好像也只能採取:我們就當作忘記這部吧。
包括鈴木敏夫,還是看到吾朗一直在模仿宮崎駿,藉由模仿父親來達成他的致敬。那樣的模仿我們覺得是不需要的,只會讓人覺得「還是逃不開宮崎動畫」的焦慮。吾朗在《地海戰記》一開始就做了一個「把父親殺死」的動作,但整部作品還是在「向我的父親打招呼」。比起所有的吉卜力後輩導演們要怎麼樣擺脫父權創作之眼的注視,如米林宏昌想像大師還在監視自己,對吾朗來說一定比其他人還要複雜得多。眼看《安雅與魔女》也是一顆燙手山芋。(笑)
陳:補充硯拓說的,看完試片的宮崎駿,在書裡鈴木敏夫有記錄下他說:「要是我也會這樣拍。」感覺得出來書裡很努力在為吾朗說點什麼。(笑)
不敗的吉卜力經典配樂「#久石讓」、「#二階堂和美」
陳:做這本書過程中,我把吉卜力的配樂都拿出來聽,YouTube上有一個吉卜力二十週年的久石讓音樂會,非常精彩!大家想到吉卜力的音樂都會說出「久石讓」,其實提拔他的人不是宮崎駿,而是鈴木先生口中「非常有音樂素養」的高畑勳。
高畑勳在七八零年代,久石讓還沒那麼紅的時候,《風之谷》製作前期就去問了。那時還有比久石讓更知名的原創音樂製作人,但他們決定起用久石讓先生,才有後來我們熟悉的,由久石讓創作的音樂。
鈴木敏夫在書裡提到:久石讓習慣先作曲,而在《龍貓》這部電影,他們先找了一個童書畫家寫了〈散步〉的歌詞,沒想到就讓久石讓卡關——通常想到吉卜力的動畫就會想到磅礴的管弦樂,可是突然要他做一首兒歌,讓他傷透腦筋。最後終於完成譜曲的〈散步〉也成了宮崎駿最愛的一首曲子,畫《龍貓》的時候,據說宮先生是邊哼著歌邊畫出來的。
Eva:我們在做專刊時,很努力找尋與吉卜力高度關連的受訪者,音樂當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次很幸運地聯繫上主唱《輝耀姬物語》的二階堂和美。她很驚訝原來台灣會想要用音樂的角度來認識日本動畫——我們身為觀眾,甚至在不懂日本歌詞原意之下都可以被深深打動。
作品還沒完成,就先找好主唱,「研究狂」高畑勳的魅力就是在這邊:他能知道自己的電影要什麼聲音。二階堂和美的歌聲非常有穿透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有重頭再講一遍故事的感覺。她坦言合作中間有很多的磨合,同時經歷了311地震,二階堂和美說自己在詮釋這首作品時,包含了日本人所有的情感,後來達成了自己與吉卜力合作的完美境界。據說後來吉卜力有再找她,她就婉拒了。
究竟「#誰是拖稿大師」?
陳:書裡很明顯看得出來,最常有的片段就是高畑勳又拖稿了。(笑)
如Eva剛剛說的,高畑勳很知道自己要什麼,但那樣的作法是很花時間的,《螢火蟲之墓》就是個例子,首映的時候據說都還沒畫上完色,直到上映當天才完成。
「拖稿大師」好像有點在笑他們,可見兩位導演是對他們的作品非常專心雕琢。還有一次又是高畑勳,因為鈴木敏夫已經被他騙過很多次,就先假裝是春天要上這部片,海報道具都做好了,寫「今年春天上映」,但高畑勳還是來不及完成,低著頭跑去問鈴木先生怎麼辦,鈴木敏夫就說:沒問題,其實跟片商都談好是秋天上。沒想到一拖,更不可能在秋天上,最後還是冬天才上。(笑)
二位有想要幫高畑勳平反嗎?
張:我們三位都編書,《釀電影》和《秋刀魚》也跟很多作者合作,對於這種──邀稿、給期限、對方會不會準時交稿?如果對方習慣性不準時,那期限是不是要先給一個……假的?──的邏輯都很熟悉,把賴床時間也算進去、鬧鐘調早一點的概念。(笑)
讀《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的前半,鈴木敏夫寫到,早期的高畑勳與宮崎駿是一個當導演、另一個就當製作人,兩個交換著做,一個畫畫、另一個就爲他掌握資源跟進度。高畑勳當製作人的時候,他是一個完美的細節控,不管是設定流程、處理預算這些能力都非常強,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矛盾的特質──擬定計畫,精確執行;但輪到自己做創作者,每一部作品都沒辦法如期完成。
我自己同時作為編輯和寫作者,其實可以理解這樣的矛盾。當你成為那個要管時程和錢的人,可以有一個清楚的、理性的、甚至不留情的一個腦袋;但作為創作者,又希望自己可以擁有自由的期限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的時候,只能試著平衡或在之間遊走,或是需要另一個人來當你的編輯。或是把創作的部分交給別人,自己去當管進度的人。這樣一個兩種性格交雜很有趣。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是漫畫家冨樫義博的粉絲,但我是他巨量的粉絲中最沒有脊椎的那種粉絲。(笑)
「你可以照你的方式把作品畫出來,我願意一直看你的作品下去。」愛什麼時候畫就什麼時候畫、要停多久就停多久、愛交草稿就交草稿──對他毫無怨言或不滿,我就是一個這樣的粉絲。當一個作者可以走到想畫的時候才畫,想畫多少就畫多少,畫不到滿意時就交不出來的境界時,他是幸福的。同時我相信:這才是產出最好作品的方式。即使會讓我們讀者等很久,可能永遠畫不完,但我知道這會得到最好的作品。
所以同樣地,我在看書的過程我同樣可以感受到鈴木敏夫的頭痛,尤其是當他要面對的不只是這個作品會延誤──發行怎麼辦?談好的戲院怎麼辦?宣傳的錢怎麼辦?還會卡到後面的作品的時間,宮崎駿已經在旁邊跳腳了!宮崎駿又是一個沒事會跑出來撒嬌或爭寵的傢伙……。(笑)
諸如此類,鈴木敏夫背上一直有把火在燒,但如果我在他那個位置,可能也會這樣寵那兩個導演,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被寵出來,我們才能有這些作品可以看。
鈴木敏夫這位製片人有多難得?在這麼困難、各方面根本無法折衝之下,到底鞠了多少躬?去人家家裡拜訪了多少次?請了多少飯局?才讓吉卜力變成今天的樣子。
Eva:日本一直以來在時間管控跟完成度都是非常要求的國家,像大家都會講:電車不會誤點啊。可是在創作上面,比如日劇《重版出來》,編輯到作者家去拜託作品一定要及時完成。日本人都沒辦法接受遲到,但他們卻願意忍受拖稿這件事?我覺得日本這國家真的太微妙了,這麼講究準時,卻可以接受在電影上映前一刻才把最後一幅畫完成──這明明就太亂來了!可是這麼亂來,卻又如此出色。
所以,會不會拖稿在日本頂尖的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本質存在。(眾人笑)
當然一開始的吉卜力是不可能更動戲院的時間,不可能更動宣傳。書裡面提到,他們最初的合作單位是像博報堂這樣的大廣告公司,不可能改動時間。可是當吉卜力從小公司變成日本最重要的支柱的時候,好像傾全國之力可以理解這件事。
這個態度的轉換,可以理解到日本人對創作者的包容與寬容。剛才聊到的「製片人得要很多事情低頭鞠躬」過程實在很不容易,也可以看成他們對於創作者的空間跟舞台,讓他們今天可以成為大師。讀《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時,我有時也會想,如果今天是台灣的創作者會是怎麼樣呢?我們有沒有辦法接受在上片前一刻才把作品完成?雜誌要出刊前才把全部的稿子收齊、版面全部完成?(笑)
我覺得這都是彼此間的角力,但不得不說鈴木敏夫「心臟很大顆」。想必他擁有強健的心臟才有今天的吉卜力。我覺得「拖稿大師」是給他們的讚譽!
整本書裡到底「#誰是天才?」
陳: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誰是天才?
我個人的心得是:能夠駕馭兩位導演的鈴木敏夫,就是個非凡的存在啊。每部作品中有這麼多找人、找錢的細節要處理,還要說服導演怎麼做、怎麼畫,甚至兩位導演吵架時,他也要居中調停。忽然想到鈴木敏夫是獅子座,或許是這樣讓他得以發揮他掌控這方面的實力。(笑)
Eva:嗯,其實我看到這題目時想了很久。採訪二階堂時,她很強調合作過程中看到了高畑勳身為導演的堅持;我們還採訪到幫吉卜力做色彩校準的公司,他們也提到,跟宮崎駿合作後,就明白所謂的純粹的藝術家到底擁有什麼樣的工作精神。我覺得他們倆在創作領域中,都各自有天才的部分。擁有藝術上的天分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可能沒辦法畫一千幅畫後就成為宮崎駿。
要去成就他們這樣的人更是困難。我們都聽過慧眼識英雄的故事──在亂世中找到一顆寶石琢磨後把它推上檯面上,能夠找到這樣的寶石很不容易,但可以去幫這些天才抬轎更不容易。像我們做編輯的,有時候會忍不住手癢想寫稿子,但還是得考量到給作家舞台,去成就他們的作品。
鈴木敏夫打造了一個舞台,讓他們發揮藝術天分,還要欣賞、包容接受他們的個性,這角色要認同天才也要駕馭天才。我原本要說鈴木敏夫就是天才,但會不會他才是「比天才更天才」的人?
張:Eva提到一個重點!能夠處理這麼難搞的兩個人,而且能夠跟他們相處四五十年,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不可思議的。(笑)
書裡提到,製作《天空之城》時,他們到處找製作公司,但業界已經在傳說:雖然他們做得出很出色的作品,但「這兩人到哪裡,那個團隊就會倒」──所有人完成作品後都會辭職,然後那個地方就寸草不生。意思是跟他們合作不只是辛苦或要求高而已。
但鈴木敏夫可以從一開始是個晚輩,幫他們打點所有事情的角色,漸漸地四五十年下來,成為他們創作上的支柱。他們三個這樣的關係真的非常難能可貴。
宮崎駿拍完《風之谷》就說過不想當導演了,因為為了拍片他跟朋友都鬧翻了,他說:「失去現實中的朋友實在是太痛苦了。」他們不會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難相處的人。宮崎駿在紀錄片直接說自己脾氣很差,尤其在創作時更是暴躁,臉總是很臭,但因為這世界不太能接受不友善的人,所以他在人前都要裝得像龍貓一樣,慈祥老爺爺的樣子。
我們做為寫作者多少能理解,創作過程中情緒通常是很焦慮,很難是開朗或陽光的。鈴木敏夫該說是駕馭,或是伴君如伴虎,陪伴這兩位老戰友這麼多年,的確很不可思議。但如果區分成「管理上的天才」,我們真的要去說「藝術上的天才」,相較於高畑勳研究狂的特質,宮崎駿絕對是個天才。
他很努力,有日本職人精神──從基本功做起,認為工作就是要從早上九點做到晚上十二點,一頓飯只吃五分鐘,到這個年紀還沒有腸胃問題也很厲害。(笑)
這樣的工作企圖心持續到年老後,還能有如此多的創意與想像。當然兩位導演也都是百分之一百二或兩百努力的典型,而才華也是無與倫比。
我自己看宮崎駿的作品時,會以《神隱少女》切分之前、之後來看。他早期會講一個完整的冒險故事,比如《紅豬》,但到了《魔法公主》,用鈴木敏夫的說法就是故事的主題提升到哲學的層次。接著他畫出了《神隱少女》這樣的作品,完滿而充滿神采,又能給予觀眾新的東西,客觀而言,《神隱少女》幾乎可說是他生涯最巔峰的創作。
之後的《霍爾的移動城堡》、《崖上的波妞》與《風起》,宮崎駿變得放開,更不在乎作品要是一個完整而封閉的體系,是一個不規則的、不斷展開的故事。
書裡說道,野中晉輔曾形容《霍爾的移動城堡》是一個「不斷在起承輪迴進展」的故事,不像之前的作品是個封閉的迴圈,變得更自由、更舒展開來。以宮崎駿的創作過程來看,以前是在創作之前就把作品所有分鏡圖都完成,簡單講,整個故事就已經想好了,接著再進行細部的作畫。但從《魔法公主》開始,他變成結局還沒想好,前面就已經開始畫了。這就造成一邊畫還會一邊改劇情,執行細節的人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的作品。而愈到後期他就愈變本加厲。在這兩者之間重疊的作品就是《神隱少女》。
前面柏昌提到,原本宮崎駿花了一整年畫好無數的概念草圖,最後全丟到垃圾桶。我們祈禱鈴木敏夫當時有把垃圾筒裡的草圖找回來,有一天能出版出來。
總之,《神隱少女》聽起來是宮崎駿靈光一閃而生出來的東西,事後回看卻是如此地完整,彷彿從頭到尾都想清楚的故事──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叫「天才」。
由左至右為:《釀電影》vol.04〈好久不見,宮崎駿〉、《天才的思考:高畑勳與宮崎駿》、《秋刀魚》第31期〈吉卜力的世界,世界的吉卜力〉